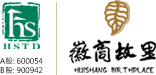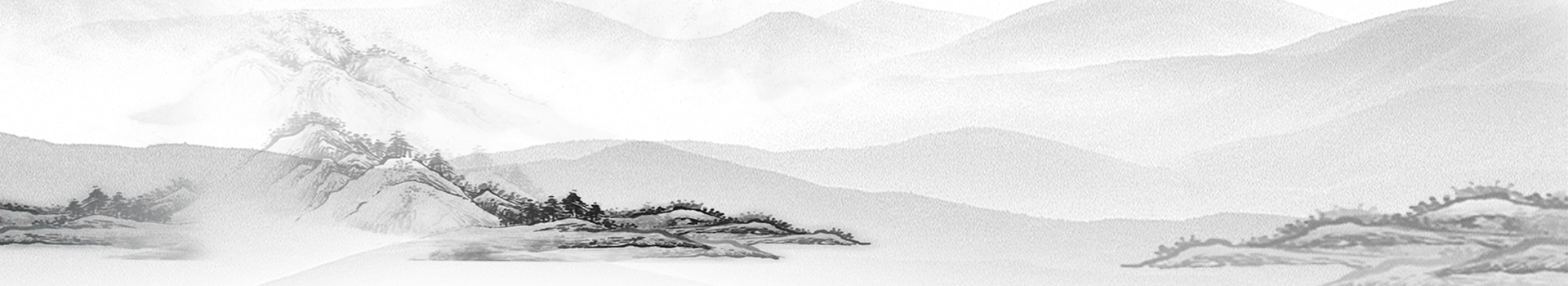明清以来,“钻天洞庭遍地徽”, 在民间经久流传的这句民谚中的“徽”即指足迹遍“禹内”的徽州商帮,它再现了明清时期这个全国最大商帮崛起称雄三四百年的历史图景。诚如史志所载:“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州诸郡”。“休宁巨族大姓,今多挈家存匿各省,如上元、淮安、维扬、松江、浙江杭州、绍兴、江西饶州、浒湾等处。”早在明朝成化年间,有人说:“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
这虽属戏谑之言,却从反面印证了一个史实,也足见当时徽商已是松江府(近现代以来为兴起的大都市上海所替代)活动最活跃、且拥有相当雄厚财力的一个商帮了。在一些史志记载里,多见有“贾松江”“贾云间”“居云间”“商游吴淞”“业贾上海”“贾于嘉定”等文字记述。譬如明代嘉靖时,休宁人邵鸾“贾云间”,独捐巨资,修复金汇、薛家两座桥,又“尝以岛夷发难,同诸父老白当路,筑邑城,愿输财筑城若干丈。”

另一位休宁人程元利“贾于嘉定……值倭围城,捐金募勇士,为诸室先,受甲登聛,城卒能保。”
正因旅居上海的徽人日益增多,他们为了合力谋求同乡的公共利益,便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联合宁国府人在上海大南门外共建起当地最早的商人会馆之一——徽宁会馆(号“思恭堂”)。此后,徽人到那个地方业贾经商的越来越多。如绩溪县上庄明经胡氏家族,大约在清乾隆、嘉庆之际,胡兆孔率先赴上海闯荡商海,继之接踵者不绝,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列肆上海者又有万字招牌十三肆,皆兆孔公派也;鼎字招牌九肆,皆志俊公派也;而余派亦称是。同治、光绪之际,则上海有贞海公之鼎茂、王庭公之万生端、贞春公之松茂”等,皆为“业并素封”的富商。降至清末,胡氏“旅居上海一带为最多,率常数百人。”
另一支宗族王氏“光绪末经商上海者尤多。”而由胡氏茶商家庭出身的名流胡适,对本家族乃至家乡人在外经商的情况知之甚明,他曾经就编纂《绩溪县志》事宜谈起一番意见:“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植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
由此可见,上海是经商活动较晚些的绩溪人外出服贾的五大区域之一,这也佐证了上海地区乃是明清徽商竞相趋赴的一块商业宝地。从所涉行业来说,历史上的徽商经营的四大主打行业是盐典茶木,这些在松江府(上海地区)均有徽商染指,尚且商绩不俗。

明朝徽州府歙县人(今属徽州区)汪道昆陈言:“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
这种情形在明清松江府的徽商群体也可见一斑。明清时期的苏、松两府正是浙盐行销的主打口岸之一,而浙盐与淮盐一样,向为势力雄厚的徽州商帮所操控,在松江府行盐的商客几乎都是徽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上海盐商汪凤翔等人联名要求官府禁止胥吏对他们栽赃陷害,状书词称:“商等俱系徽籍”,“远挟重赀”营运于江浙之间。
明末清初,“原籍徽州”“原籍新安”的商人程嘉宾与张式之均在嘉定县行销盐业。
清末黟县宏村大盐商汪定贵于同治、光绪之际除在扬州、汉口、渔亭设源顺盐号及盐店行销食盐外,还在松江购置店堂,常驻职员,来往于浙杭、两淮、申浦之间,做成红火的盐业生意,他在从事盐业同时,还利用返回空船捎带各地名特土产,异地销售,获利颇丰,富甲一方,“亿则屡中,佥曰良贾”,跻身于徽州巨贾之列。
徽州盐商的财势很是兴旺,形成徽州商帮的中坚。徽商经营的其它众多行业,往往是在盐商的大力支持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明清徽商在松江府的活跃,与徽州盐商势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明清徽商在松江府经营典当业的也很多,且手段相当高明。据汪道昆《太函集》载述:明末徽商吴继善“之吴淞,以泉布起”,汪海其人则“以质剂息子钱,一居云间,一居东省”。郑桢“贾松江,权子母。不数年间,赀财稍裕,家道渐兴。”

而清初华亭县人董含也在其陈说乡里之事的《三冈识略》里记载:“新安有富人二:一程一汪,以贾起家,积财巨万。以重利权子母,持筹握算,锱铢必较。”这两个在华亭一带开典当铺的徽商仅是当地徽籍典当商人的两分子,其实在那个地区从事这个行业的徽商世代继有,直至抗日战争前夕仍然是“朝奉司当赎,多徽州籍。”
这些徽籍典当商不少是善于经营的好手,有的在长期经营活动中积累了早期金融理财的丰富经验(包括鉴定银两真伪及其成色的经验)。如明末歙商汪通保当年在松江府创开一家典当铺,“乃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诸子弟四面开户以居,客至则四面应之,户无留履。处士(汪通保)与诸子弟约,居他县无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于是人人归士如流,旁郡邑皆至。居有顷,乃大饶,里中富人无出处士右者。“
汪通保深得生财之道,他以种种优惠条件吸引顾客,使自己的当铺越开越大,分店愈建愈多,不但在其故乡堪称首富,在商贾之地松江府也是屈指可数的富豪人物。此即徽商业典成功的一个实例。徽州典当商人的活动,固然曾使一些小生产者深受盘剥之苦,但客观上也发挥了调剂资金的作用,适应了小生产者的需要,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还是有些助益的。另有黟县三都人汪联洪(元治),利用自己在鉴定银两真伪及成色方面的专长,于清光绪初在上海创设了公估局,此后,凡银炉所制宝银,必经公估局加批重量与成色方可在市面上流通,这对那里的金融市场一度起到了良好的调控作用。
明清之际,徽州所产茶叶(特别是休宁松萝茶)就已驰誉苏松诸府。“徽茶之托名松萝者,于诸茶中犹称佳品。顺治初,每斤价(银)一两。”
这大抵相当于一石米的价值,足见其名贵。徽州人所卖的珠茶、雨前、熙春等品牌的绿茶以及祁门红茶均为畅销海外的名茶,也深受上海消费者的青睐。尤其鸦片战争前后,徽商在松江府经营茶业就颇负盛名,非常得势的徽州茶商成为上海商界最活跃的力量之一,可说近代实力最强的徽商首推茶商。他们将徽茶运抵上海,再装上沙船,往北方远道销售,或“素投茶栈,转售西商”, 销往海外市场。清光绪时“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
据统计,清代光绪二十一年(1895),徽州外销的绿茶和红茶共达11万引,约合1320万斤。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徽商运往上海销售的。在上海,徽商纷纷设茶号茶庄,开茶店茶栈,办茶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清末民初仅绩溪人在那里就设有33家茶号,而到抗日战争前夕,歙县人在沪经营茶叶的商号更数以百计。
这其中如黟县人在天津路开设的“公兴隆”、绩溪上庄余川村人汪立政于清咸丰元年(1851)在河南路(上海旧城老北门)开设的“汪裕泰”等都是经营绿茶出口贸易的著名茶栈。“汪裕泰”规模最大,下设6个发行所,经营30多个品种茶叶,号称“茶叶大王”。而祁门人在北京路开设的“洪源永” 茶栈则专营红茶出口贸易。
至于茶厂,清光绪二年(1876)就有祁门人胡元龙创建日顺茶厂,其它茶厂也纷纷兴办,经营者“大都为安徽、广东、江苏三省人,而尤以安徽人为最多,上海之著名茶厂及大部分资本均属之。”
茶厂中的工人和技师大多是徽州人,他们掌握着一流的技术。清光绪二十年(1894),浙江省“永嘉茶商为扩充洋庄茶之营业起见,先向上海聘请徽帮茶司,分入平阳南北港各产茶地宣传指导,将毛茶坯改制炒青,运销上海,去路大旺。”
木材贸易向来属于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而徽州木商中在明清时期的松江府多为婺源人所经营。当时大批徽商从皖浙及川贵湖广赣等山林地带运出木材,分别沿着钱塘江和长江水路集放在杭州的侯潮门外与南京的上新河,又由此二处转运至上海(绝大部分均如此)。清初松江府所立的禁碑称:“本郡四门木竹商人程泉、程召、李全、汪塘等呈称:泉等俱属徽民,远贩者投治……看得木竹行业尽系徽民,挈资侨寓,思觅蝇头,冒险涉远,备尝辛苦,始得到埠。”
除此盐典茶木而外,徽商还在松江府经营造船、棉布、丝绸、油漆、徽墨以至皮草、杂货、饮食,范围可谓相当广泛。
徽商的木材贩运活动促进了上海地区的造船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建造能够航行于江河湖海上的船只所用的坚材巨木几乎全部由徽商供应。“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
这种造价最昂贵的沙船船体大,数量多,行驶于北洋,专走牛庄、天津等处,此外还有南船、卫船、宁船、鸭尾船,它们由上海港口出发,分别专走山东各埠、福建南洋、浙江宁波和长江水道。安徽商客金某还“赉资本至浏河,始创造海船。”
该镇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码头,“东省徽籍以及通属各省商人”麋集于此,经营海上贸易。其它如吴淞口亦是。清顺治六年(1649),江宁巡抚王国宝奏称:“看得洋商乔复初等,其籍另据《海运新志》载:明末,‘海禁久弛,私贩极多。辽东、山东、淮扬、徽、苏、浙、闽之人,做卖鱼虾、腌猪及米豆果品瓷器竹木纸张布匹等项,往来不绝。’”

入清以后,“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
其中布茶正是徽商所经营的主要商品。有山陕徽浙籍商人,“于明季弘光元年三月初一日纳税给引,由定海出关。初十日,吴淞挂号泛海而达日本长(岐)崎。因传鼎革,流落异域。欣闻本朝柔远惠商之政,于今年正月初三日由日本开行,二月初三日过稗沙,初六日收泊吴淞。所携货物,俱于长(岐)崎贸易而来。”
明清时期的松江府是全国棉织业的中心,棉布乃是沪地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之一,“松民贸易半仰给于纺织”,可见棉织业之于当地繁荣发展显得举足轻重。而那时松江府城中有许多布商字号均为徽商所开。
清乾隆元年(1736),就有四家徽人布商出现在府衙所立的禁碑(禁止苏州布商冒立字号)之上的署名行列里。某吴姓徽商自称“原籍新安,投治西外,开张富有字号,在郡门市居多。”
其时到清末,上海县城还有祥泰、余源茂、恒乾仁等许多徽商开设的规模很大的老牌棉布字号,且“字号在松,发卖在苏,且牙行亦多居松。”这表明,每一字号往往设立许多分店,采取商牙结合的经营方式,在城乡各地广收棉布,或直接运销外地,或经本字号染踹加工之后再行发卖。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上海青蓝布业公所规定“各号发布,无论本地、浏河,每包捐银叁分”,以备公用。这说明除了苏州外,松江府的棉布许多是在浏河口以及吴淞口直接装上沙船,由海道北运或转销外地的。实际上,在松江府许多盛产棉布的市镇,明清以来,为数众多的徽人布商就从未绝迹:成化时,歙人郑富伟“东游吴淞,北寓临清”;
徽商汪应选“迁居南里(南翔镇),足迹历蓟门、辽左”;历时,“新安布商持银六百两,寄载于田庄船,将往周浦”;在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徽商辏集”;而在外冈镇,“四方之巨贾富駔,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其中贸易花布的主要是徽商,“外冈布,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大场镇“山陕布客、徽商等来此坐贾……收买花布,非至深夜不散。”
这些市镇上的徽商,或为松江府、上海县等处字号代收棉布,或由自己独立营运,把棉布的收购、染色、运销连成一体。徽商的这些经营活动,实现了松江府所产棉布的外运销售,同时也通过市场机制提供了当地百姓所需的棉花及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从而为该地区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近代上海丝绸出口贸易中,徽商也占有重要地位。湖州、苏州、嘉兴等府盛产丝绸的城镇历来就是徽商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之中涉足丝绸大有人在。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成为丝绸外销的主要港口。
1846至1859年间,上海丝绸出口量占全国的81%到100%,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湖州等府。民国《南浔志》称:“……小贾收丝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指外国列强)正通商,废话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
清康熙时就移居南浔且靠丝盐贸易致富的休宁张氏家族出了张颂贤,他就是这些大小丝绸商人中的一个。他专收蚕丝售给西国洋商,积赀达到1200余万两,成为当地财力最雄厚的富豪。
而富甲江南的“红顶商人”胡光墉(字雪岩,绩溪胡里人),却在商战中带头抵制列强侵略,他曾经邀集华商,凑齐本银2000万两,尽收全国蚕丝,不使一丝流入西国洋商之手。尽管洋人再加价1000万两,他也不允许,使得西商恼羞成怒,于是相约当年不售蚕丝。到第二年,新丝上市后,华商因为财力不济,被迫仍按洋商的条件出售蚕丝。、
除茶丝生意以外,徽商在上海经营的其他行业还有京广南北杂货(歙人),草货、皮革、土布(黟人),木材、油漆(婺源人),墨业(绩溪人、婺源人),饮食业(绩溪人),都在上海商界占有重要地位。享有盛名的徽人墨商在那里开起“胡开文”“曹素功”“詹大有”“二妙堂”等墨店,几乎垄断了徽墨贸易。而精于烹饪的绩溪厨师则开设了大东门“大辅楼”、海宁路口“海华楼”、小东门“醉白园”、九江路“太和园”、福州路“中华第一楼”等,它们都成了上海滩著名的徽菜馆,烹制的徽菜别具风味,深得顾客的赏识。
综上言之,明清时期的长江流域乃是徽商活动盛行的最重要区域之一,整个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众多大小城镇几乎都成为徽商辏集之处,沿江一线的大多重要的商品贸易也被徽商操纵在手,因此,许多徽商通过商贾生涯的成功打拼,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积累起巨大的商业资本生动地演绎着这些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史。